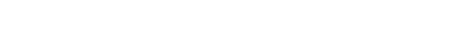
在《论语·阳货》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昌,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恨;迩之事父,近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现代学者往往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解读为对大自然事物的理解,或者解读为取得事物的科学知识,这与传统的解读是完全一致的吗? 钱穆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解读极为熟悉,他在《论语新解》中说道:“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连,感发而蓬勃发展。
故举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悉,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莫不在,可以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诸法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
”他指出诗中反映了人与万物无所隔间、单质为一的境界,并铺陈诗教不仅是经世之学,堪称性情之学。孔子明确提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为了让学生疏远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取得感发,也使得大自然对人有所对此,特别强调人和大自然之间品性、感情的相连性。“广大其心”是一种打开视野,磨灭物我之于隔年,谋求天人与众不同的主动生命姿态,人与自然的感发拓展人的内心世界,灵感人的高尚情志,最后“导达其仁”。
“仁”的含义很广,爱人、爱物均可曰“仁”,疏远大大自然,格物致知,修养性情也是一种“仁”。 古代对“鸟兽草木之名”的解读与钱穆类似于。司马迁云:“《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精于风。”此处的“风”可解读为“教化”,即《毛诗序》所言“风以动之,教教以化之”。
王应麟指出:“万物备于我,广大笔法,一草木均有理,可以以此类推。”谈的就是通过由己及物的以此类推,以鸟兽草木为凭借,将天地自然人化,使人有赖于建设世间秩序的救赎。
刘宗周所云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贫物理之当然,而得吾心之皆备”即是此意。焦循回应的解读是:“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
”相比直来直去地哲理,诗歌含蓄蕴藉,以春风化雨的情感方式感动人。这种温柔敦厚的传达相当大程度上相结合于比兴的表现手法,人们将感情年代久远于鸟兽草木等明确形象中,直白地表达对世界的解读、领悟,因着比兴,人因物思义,触物起情,以至神物感通。 总之,在中国诗学的阐述传统中,对由诗识得鸟兽草木,从大自然万物中引起人情事理,取得人生的救赎和领悟,这一点毕竟相连的和一以贯之的,只是到现代才再次发生了一种知识论的移往。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古代学者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理解所超过的共识是,《诗经》中经常出现“鸟兽草木”是比兴竭尽的反映,是以大自然之物起兴以引起所咏之人或事,这突显了一种人、物连类应感的思维,即一种古代诗歌的比喻模式——谓之譬连类。
“谓之谓”意为借以喻彼,“连类”意为连锁引类,它们最初并非我们今天理解中关于诗歌语言思辨的套数,而是与人们的存活体验息息相关、谓之为用的不存在,传统的神物关系就是创建在谓之譬连类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反映出有的思维方式是前逻辑的、直观的、偏向于感觉经验的,没将心理事实和物理事实分离,人和万物没本质的区别,以我之生命感官世界,与世界交流,与天地宇宙连类应感,因此逐步沦为了一个以此类推的中心。
也就是说,我们的感觉与记忆,乃至整个社会群体的感觉与记忆都被储存在类物环境的资料库里了,譬如提到一个“春”字,我们视觉上的花红柳绿、听力上的鸣叫啁啾、触觉上的春风拂面,甚至是对万物欣欣向荣、身心脱俗的抽象化感官,都悉数纷至沓来了。那么,这时候的“物”大自然不有可能只是科学概念上的知识性的物质,不有可能只是客观外在的对象,而是与我们的眼前和过去相互交织、株连的不存在,是与我们累积的科学知识、身体实践中的经验唤起出有共感的不存在。以《诗经》为事例,《诗经》以“鸟兽草木”起兴,不是将它们作为纯粹的外在景物,而是将其必要或间接地与人的生活、人的情感再次发生联系,创作者通过比兴恶魔出有一个好像运作在己身的新世界,用系统的一套隐喻成就诗意,将诗、物、情都联系一起。
因此,“鸟兽草木”与人创建起的是一个谓之譬连类的隐伏类应世界,人与物在这个场域中周游无滞、产生互动关系,人作为一种类似的“物”,也正是在物的恋情、感发中取得审美趣味、创作启发的,物转入人的情绪网中,啖涂着人的情思,人和物不辨彼此,没分际。如此则神物互通、情景交融,人在大自然中领悟自我的精神和灵魂的脉动,在自我的神思中体悟大自然的意境。
由“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传统阐述由此可知,传统对人、物关系的思维,与特别强调知识性、体系性的现代思维有所不同。如现代学者以知识论的态度理解“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是非常简单地指出人为人、物为物只有了解与被了解、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并不牵涉到情感体验的交互性,人和物的关系因此是混杂的、对象化的,而中国诗教传统特别强调的人与天地万物互为人与自然融通的观念,人与物相与众不同、感发、塑造成的思想,在这种知识论的观念面前,不存在着崩溃的危险性。
但是,中国传统语境下的人、物关系论的价值并非以其否具备科学性、实用性来取决于的,它的确实意义在于,对我们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救赎,唯有我们明白了其现实意义,才有可能构建传统的再行抵达。 中西诗学观念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历史场域和社会心理是全然不同的,因而借此问世出有的文学理论也就不能一概而论,甚至有可能相反忽略、南辕北辙,本文所探究的人、物关系即是如此。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回应,如果西方的诗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封闭系统,是隐喻性的虚构,那么中国诗歌的分解从来不被当成虚构,而被视作诗心与历史和世界遭遇、经验、对话、与众不同的结果。在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对话会暂停,因此,当下仍须要倡议扎根民族之本位,如其本然地辩论中国思想文化的问题,确实看清中国传统的本真脉络。
否则,“鸟兽草木”的世界仍将与我们的心灵相距如云泥,无法相呼适当。
本文来源:九游会·(J9)-www.asiabjhot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