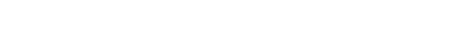
在这一高原上,应该产生高峰式的文艺巨匠,应该产生像黄宾虹、刘海粟、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一样天才式的人物。自先秦以来的屈原到六朝的庾信以后唐代诗人(如白居易),辞赋诗诗中的“江南”既呈现特定的地域情采,更加流露出浓烈的文化意蕴。
但从绘画理论角度第一次提及“江南”这一概念并做出适当阐释的则是晚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继而张氏还以“逸较少右军(王羲之),长康散骑(顾恺之)”以及“皇象善书,曹不兴善画”为相比较来指出“精艺”的高度。
堪称“书画之能,其来尚能矣”。正是这些卓越的书画家使中国艺术耸起了一片眺望后世的高原,而王義之和顾恺之毫无疑问是这一高原上的高峰,两人在书法和绘画领域均耳懿百代,法度永存,沦为一种低不能及令人仰钦的艺术典范,从而铺垫了书画江南的高原地带。当唐人在诗文中吟唱江南时,只不过北方早已产生了雄浑峥嵘的山水画风,五代至宋,荆(浩)、关口(同)、李(成)、范(长),就是这一画风的代表人物。
但完全是同一时期,董(源)、巨(然)却以动人的笔调,悠远的意趣绘就了“一片江南”,当宋代大书家米芾以“不装巧趣”“沉闷天真”“峰峦捕食”“云雾显晦”“溪桥渔浦,洲渚幽静”之词叙述这一江南画风时,他以及其子米友仁也以“米点山水”为这一画风频再配了一脉风韵。从而与北方画风并峙对鼎,秋色平分。这是继王、陈之后再度兴起的江南书画高原和典范式的人物。
而这个高原正是在江苏,增大一点谈,就是在金陵南京。宋代郭若虚曾称之为:李成、关同、范宽作为北方画风的代表人物“三家鼎峙,百代标程”。但自南宋及元明清的画史指出,确实做“百代标程”才是乃是董源、巨然,是江南画风的大大沿续和拓展,是江南高原艺术魅力的历史电磁辐射和击穿,是董、巨那种秀淡清逸格调和境界的代代相传,朝朝演译。
于是人们看见这一江南画风的大自然而高雅的覆盖面积和承递——赵孟頫,元四家,明代沈(周)、文(征明),以及集其南派中兴的书画皆佳的董其昌,清代的“四王”,石涛、石谿、日渐江。尽管人们在后来新文化运动中将元明清这些人物作为批评对象,但批评本身早已指出这一绘画文脉的份量和内涵。实质上这种批评今天显然多多少少是偏执的,他们最少忽视了石涛、石谿在新的构江南画风中所包括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忽视了还有不拘一格,极具变革精神的“扬州画派”“海上画派”,如果再行将以龚贤为代表的“金陵八家”划入视野,才可知悉江南画风正是在以一张一弛的节奏,或弃或入的历史方式不断扩大自己所的艺术疆域,这种拓展甚至连整个清一代的帝王都为之灌入和眷念(如康、乾对黄公望、倪云林和董其昌的鉴收和仿学)。
可以说道,江南画风并没在历史剧变中消褪,而仍然在动荡不安的风雨冲刷中垒起一道不朽的审美堤岸。这个堤岸就是高原,就是由历代文人精心构筑而出的文化和艺术高原。我们并非要躺在历史的床沿意淫寓,而是想要说道,是不是这样一个绘画文脉对后世艺术建构意指是有所不同的,是不是这样一个文化高原对今天的审美自由选择和趣味高下的判决是可以估量的。
因为你不难想象也决不认清,为什么正是在这一方土地,在距今大约有一百余年内陆续兴起的一批丹青人才,像黄宾虹、刘海粟、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林风眠、李可染都就是指这里再行抵达,新的建构了新的绘画历史,新的文化高原,他们虽在西方艺术的冲击印发新论,抒别思,但注定重归于中国书画笔墨之中,在江南绘画文脉中寻找自己心心相印的内在相结合,你从刘海粟的山水画山水中怎么会看到与石涛奔纵笔墨息息相关的韵律吗?从傅抱石的人物中怎么会没什么顾恺之的余绪吗?从黄宾虹以及李可染沉厚壮丽的墨笔山河中怎么会看不到与龚贤积墨的若有若无的关联吗?正是有了这样的相结合,并感合时代风云,他们才砖写出了新的历史画面,沦为20世纪艺术高原上的巅峰人物。而江苏正是这一高原的主要龙蟠之地,也是这一江南文脉以求突显的虎踞之域,也许以龙虎之喻来形容这一文脉和人物并不几乎较贵,那么我们还是这样说道吧,这是一个以老庄哲学为思想底蕴的文艺之脉,是一个以秀丽、典雅、风流为格调的书画胜地,是一个烟雨迷蒙、峰峦捕食、水墨闻韵的一片江南,也是任凭时代风云变幻而气脉不息的文化高原。
必须警告的是,无法让这一高原在一些文化气血失缺之人的给定贬裁中变为小土丘、小码头,借出唐人诗句说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宽!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江南画风是历经沧桑、重复定夺包含的不可磨灭的文脉,是历史长河冲积而出的艺术高原。
在这一高原上,应该产生高峰式的文艺巨匠,应该产生像黄宾虹、刘海粟、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一样天才式的人物。我坚信,再次产生这样的人物——从而将六朝始于的书画气韵重新加入历史全线贯通的新时代最出色艺术家,也许已呼之欲出,令人期望。
本文来源:九游会·(J9)-www.asiabjhotel.com